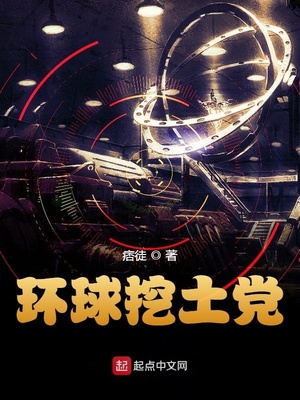逆战阁>黄粱 > 第044章 运(第1页)
第044章 运(第1页)
这本该是黄清若的护身符,二叔公往她身上赋予的价值,是她这两年能被梁晋东的子女放过、安稳地在国外念书的原因,也是往后她于梁家之中的立足之本。
而她现在跟梁禹说自己毫无用处,等于丢掉了护身符。理性来讲,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。
走出医院的时候,黄清若望着阴沉沉的天空,心想:她还能好好地待在霖江,等到黄薇出狱吗?
-
辗转了几趟公交车,黄清若成功抵达修车厂,领走自己的车。
车没买多久,之前一次换车胎和这次修车,所费的这些钱,割得她肉疼。
于是下午在工作室里修复瓷器,她也就更专注了。
专注得又没能察觉时间的流逝。
少了丁渭的提醒,黄清若自己回过神来时,竟然快十点钟。她驱车回到半山别墅,则将近十一点。
上楼发现她卧室的门是敞开的,黄清若有所预感地走进去。
房间里虽然没开灯,但不影响她看见站在窗前的梁京白,整个人比月光还冷薄两分。
“抱歉,六哥,我回来晚了。”黄清若刚记起,今晚是第七次,也就是最后一次针灸的日子。
当然,她心底认为她并不需要道歉,原本这个针灸疗程就是他单方面强制性发起的。
她打开灯。
梁京白转过身,望向她:“还敢去那家公司,是生怕梁禹查不到,你在干什么?”
黄清若滞于原地,安静了几秒钟,说:“看来六哥很清楚我在干什么。”
梁京白淡声:“不想被我清楚,就安分点,少干点蠢事。”
“都说我蠢了,我又怎么能分辨,哪些是不该干的蠢事,哪些不是蠢事?”黄清若慢慢地走近他,“请六哥指教。”
梁京白没听见她的问题似的,反问:“你很缺钱?”
这不是废话?他是觉得,她住在半山别墅里,衣食无忧吗?黄清若驻足在他半步之外的位置。
她也当作听见他的问题,自顾自探究:“被你用一个烟盒困在这里,是蠢事吗?任由你在我身上要针灸就针灸、要拔火罐就拔火罐,是蠢事吗?你要我伺候你我就伺候你,是蠢事吗?我现在这样跟你讲话,是蠢事吗?”
梁京白同样并不受她的影响,继续说他的:“缺钱的话,与其在外面接私活,不如在我面前多脱几次。”
“原来讨不到烟盒,能讨到钱?”黄清若面露恍然,声音带着清霜的质地,“六哥怎么不早告诉我?”
她寡廉鲜耻地问:“知道接私活开给我的价是多少?六哥你又能给我多少?太低了,我可看不上六哥给的活儿。”
梁京白垂眸睨着她,隔了好几秒,吐出一个字她听腻了的字眼:“脱。”
最后的一次针灸,最疼。
他收针之后,黄清若拉高肩膀的衣服:“这个疗程到此为止。希望六哥不是言而无信的小人。”
梁京白收拾着针灸包,冷不防丢出话:“回霖江博物院工作。”